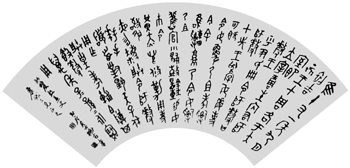
谢觐虞 篆书扇面
中国文化史上,确有众多艺术家福寿绵延,颐养天年。他们常在弥坚笃志的暮年为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佳构。正如唐代诗人李商隐吟唱“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然而也有不少才华横溢的人间奇才,由于各种不幸的原因而英年早逝。生命虽然短促,但传世作品依然熠熠生辉,璀璨夺目,同样也给人世间留下宝贵的财产、深切的回忆与思考。本文所写谢觐虞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
一
谢觐虞(1899-1935)字玉岑,号孤鸾,江苏常州人。工书能画,尤长于倚声。早年从钱振锽(1873-1944,字名山。江苏武进人。道德文章,驰誉大江南北。书法挺拔,人所珍爱。每逢乡梓灾荒,辄卖字代赈,为人称道。偶写墨竹,清标脱俗。有著作二十余种传世)问学,其以勤劬睿智为老师所赏识,遂许以长女素蕖。他成名后与张大千、徐悲鸿、王蘧常、胡汀鹭、夏承焘等相友善。著有《孤鸾词》、《白菡萏香室词》(按,菡萏即荷花)等。若评其一生业绩,词名大于书名,书名大于画名。书法尤以篆、隶为工,所书钟鼎金文,论者以为“可胜缶翁”(指吴昌硕),这当从其气格的高古典雅而言,不过是“仁山智水”而已。其画多逸笔,水墨清淡,极疏简之致。张大千誉为“海内当推玉岑第一”,同样也是就其格调的古雅绝俗而言。
谢觐虞病殁后,谢稚柳有《先兄玉岑行状》一文,对其家世、治学求艺、交游等均有阐述,兹录于右:“先兄觐虞字玉岑,先父柳湖公长子也。先伯父仁卿公无子,以兄嗣。吾家代有文学,详见家集。兄早慧,父远游,家书至,先王父养田公必令兄朗诵于侧,不讹一字,时才八岁耳。故甚为王父所爱怜。逊清光绪丁未,王父殁后四年,父及伯父一岁中又先后殁。时兄年十三,累遭大故,哀毁骨立。又两岁,火焚其居,累世所藏图书金石文房之属荡焉无存,家以中落。赖先王母、吾伯母及吾母之抚养得以成立。王母,钱名山先生姑也。兄稍长即令游名山先生门,先生逊清名进士,光绪末弃官自京师归,讲学寄园,从游者众。兄及门,三年尽通经史,为文章下笔瑰异,篆分书追秦汉,不同凡近。名山先生甚奇之,妻以长女,即吾嫂素蕖夫人也。吾家无恒产,生计惟兄是赖。癸亥秋,兄南游永嘉。受浙江第十中学聘,讲授文学。弟子数百人,翕然悦服。尽识永嘉瑞安文学之士,唱酬甚乐。暇日登谢客岩,拜康乐公之墓。永之人以兄之文采,庶几追踪康乐,叹为盛事。居永嘉一年,念王母年高,不敢远游,应王培孙先生聘,来海上主讲南洋中学文学。培孙先生雅重兄,馆之甚久,然兄年弱不宜教职,多疾疢,医者数以为言。戊辰冬,以友人招,任职财政部苏浙皖区统税局,后又兼国立上海商学院文书主任事。兄素好学,自入世途,益自惕励,公余则披阅文史,随手摘录成帙,临池或至深夜不倦。自是学大进,声誉日起。尤以书法及倚声,知名当世。海内名士多倾盖与交。前辈如归安朱彊村、华阳林山腴、番禺叶遐庵、金山高吹万、吴江金松岑,皆盛称其才,结忘年交焉。然兄丰于才而啬于遇,多病不胜医药,尝患咯血,久之乃愈。少本旷达,不善治生。然天性纯厚,事亲孝而友于弟妹。既长,自审仰事俯蓄之重,业业不敢自豫。自奔走衣食以来,十余年未尝小休。由是体益弱,每岁必数病,既不获休养,病亦不能尽去,则力疾事事,终年不废药石。甫壮而元气已衰。独居深念,索然恒有忧思。然兄仪容俊朗,清言对客,终日不倦;或议论风起,庄谐间作,一语既出,四坐为之倾倒。不知者以放达许兄,未尝知其忧之深也。壬申春,嫂免身得女不育且病,病日急。时倭贼犯沪,道阻,兄间关归里,疾已不可为。自此神伤不解,痛悼之情一寄于词,置号别曰孤鸾。画友为写《菱溪图》及《天长地久图》,兄为哀辞五千言书其上。去岁甲戌五月,王母殁,兄哀甚。体益衰……清明后形日枯槁,延至三月十八夜十时,竟别双慈弃弟妹而长逝矣,年止三十七,呜呼痛哉!病中足不逾阈,气弱不能多语,然尺牍酬答如平时,书法矫捷无一毫衰病态。弥留亦无所痛苦,且始终不自以为不治。惟日索朋好书画为乐,求之且多急,则又若自知不起,欲多见故人手迹以当永诀也。恶耗所至,识与不识,莫不痛惜,故归来吊者皆陨涕。兄于书如有宿慧,幼时涉笔即茂密恣肆。初学小篆分隶,法度既备,进而为大篆及三代金石文字,凡鼎彝尊罍戈瞿量度碑碣瓦砖以及殷虚甲骨文、流沙坠简之属,靡不致力。故其书气局闳博,不名一家。近岁喜作晋人行草,俊朗如其人。又以书法写松梅山水,名手多叹勿如,以为在雪个、穆倩之间。词自幼即喜为之,及居沪上,与彊村老人游,时从探讨,取径益高。然为多作,悼亡后始屡为之。其精诣之作,誉之者谓出入两宋。然兄常自病其词颇类清人,思力学焉,困于病不果。于诗自以为非其长,然所作近体短章颇为人所传诵,以为清丽似渔洋,沉俊似定庵云。早岁治骈体文极工,气机流畅,近简斋;后宗六朝,取法徐庾,然用情思太剧,体气不胜,壮岁屏不复为。兄既无年,终其身复困于病,不能备志于学,所诣未能尽其才之十一。使兄生长华腴,不以衣食劳其形,不以疾病短其气,优游文史,怡情翰墨,适其性之所适,以养其生,则其天年岂止于此,而其学之成就亦必有什百倍于此者。天既与之以才,乃靳其遇与年,使不获竟其所诣。天之生才果何心哉!果何心哉!兄平生所作,多不存稿。近者同学至友将为征集其全,付刊以行世焉。稚少不更事,不足以知兄之生平,率次其行谊如右,敬求当世文章道德之士,俯念先兄才命竟止于斯,锡以铭诔,以光泉壤,感且不朽。稚敢不九顿首以谢!期服弟谢稚柳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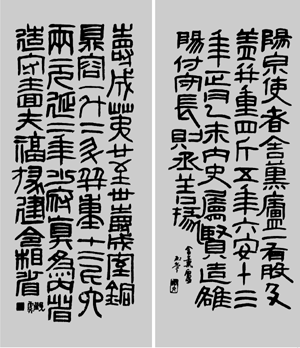
谢觐虞 隶书轴
按传统习惯,稚柳先生为兄“行状”一文定是书法佳构,然年代久远,后人不得亲见也。此时,稚老刚“而立”之年,用典精当,文笔老辣,情真意切,读之为之动容,潸然下泪亦在情理中。上世纪80年代后,我们读到稚老不少书画题跋与金石论著之序言,皆不过千百字而已。如此情挚幽深之长篇,殊难以赏目。笔者有意笔录,可见谢氏昆仲情谊,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侧面让晚生深谙古人所言“求其明道术之指归,汇众流于一脉,能为网罗整齐之说,洞明利弊中失之所以然者”。人所共知,上世纪中叶后,稚柳先生在金石书画界之声望,尤其于字画文物之鉴定,闻名于世,人称“南谢北徐”(徐即久居北京的徐邦达先生)。这与他早年厚实的家学,见闻之广博是密不可分的。
清代学者章学诚谓:“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原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通俗地说,“通方知类,以不变应万变”,对照谢觐虞、谢稚柳二老在求学治艺上的业绩,对我们后辈是有深刻启迪意义的。
二
我们注意到“行状”中提到朱彊村(1857-1931),他原名祖谋,字古微,别署沤尹。清光绪九年进士,官至广东学政,未变节降敌前的汪精卫即出其门下。后来研究词学的吴梅、龙榆生等皆列此老门墙;其弟子还有叶遐庵(1881-1968)字誉虎,原名恭绰,又名袷甫、玉甫。叶氏致力于文化艺术、保存文献古迹,文字改革等,业绩丰厚,口碑甚好。唐圭璋先生说过:“近百年于文化史第一贡献者是蔡元培,第二即叶恭绰。”至于林山腴、高吹万、金松岑皆当时名流学者。他们的人格精神与学养对谢觐虞是影响至深的。它也说明一个学者、一个艺术家绝不会仅囿于师门,而是要博采众长的。
作为学者、艺术家的谢觐虞,与其艺事交流的好友中,有几位是值得称道的。在他未病故前,徐悲鸿有函致玉岑云:“玉岑贤兄足下,弟自平归,知兄大病,深以为念!上月赴沪,欣悉尊体日就复原,弥觉快慰!今得手书,如闻謦欬,益令我雀跃无已也。弟生平不画扇,花卉尤非所长。尊命二难兼并,实深惶悚!使兄不在养疴,必不献丑而贻讥大雅,恳勿示人,传作笑柄。曼青兄(按:即画家郑曼青)想常晤面,彼昔为亚尘(按:即以画鱼著称海内外的汪亚尘)得名山老人书联,真是杰作。弟亦有数联亦甚佳,但损其精。兄暇中请为留意。弟可照润。最精者乞书上款。十联八联,或大或小,不嫌其多,惟愿得精品耳。敬祝健康!弟悲鸿顿首,三月五日。”孰料不久,玉岑仙游,徐氏有挽诗叹惜英才早逝:“玉岑稚柳难兄弟,书画一门未易才。最是伤心回不寿,大郎竟玉折兰摧!”而“回不寿”典出孔子弟子颜回(按:颜回年三十二而卒),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张大千与谢觐虞的友谊也极深厚。张氏有《黄水仙花图》赠谢稚柳,跋云:“黄水仙花最有情,宾筵谈笑记犹真。剧怜月暗风凄候,赏花犹有素心人。乙亥十二月廿日,从故都南迁,车中梦玉岑。故人仿佛生时神态,憔悴有病容。同坐一废园棠棣树下,阴气袭人。风乍起,树枝作盘旋舞,飒飒有声。身旁有黄水仙数茎,因语玉岑曰:归有题予所画此花一绝,但记其前二语矣,后半尚能续之否?玉岑逡巡不答,予漫吟续成之。时风益凄厉,月色昏暗,瑟缩作寒噤而醒,口头犹讽咏不辍也。呜呼!玉岑死将一年,予以饥躯流转黄河南北,玉岑三入予梦,而以此悉为最清晰。枫林关塞,故人之灵无时或离,予以伤心又岂特车过腹痛而已耶!庚子新正,稚柳二弟来过,因话前梦,遂作此图并记,大千爰。”魂系梦绕,情必有所思也。
上世纪20年代末,浙江省温州第十中学有两位名闻遐迩的国文老师即谢玉岑与夏承焘。所作诗词不胫自走,为时人所传诵。二公一时瑜亮,顿成莫逆之交。夏氏在词学研究上颇有建树不仅后来是大学名教授,到上世纪80年代,夏承焘与唐圭璋两位老先生为学术界并称“当代词学大师”。使后人联想到谢氏若天假以年,也必成大器也。钱璱之先生有《记夏承焘先生的七十二封手札》一文,仅选一二:“1929年5月17日,发玉岑上海一函,问朱彊村先生寓址,拟以梦窗年谱寄正也”(按梦窗即宋代词人吴文英);“1929年10月26日,灯下作玉岑书,告符文作古,问陈匪石《辛周词笺》体例及借《声律通考》,并告以小蒜大蒜治肺病法”等,友谊以外全是讨论词学,老一辈的风尚让后人敬仰。
三
二十年前,笔者撰写《民国篆刻艺术》书稿时,在南京图书馆觅到篆刻家朱其石于1930年辑自刻印《抱冰庐印存》时,发现有谢觐虞的题辞,实以篆笔写汉隶饶有金石气,结字宽博,气势开阔,掺以简牍、经卷之古朴,放眼望去绝是谢氏所书。远比《当代名人书林》、《民国时期书法》收的那幅从《石门颂》演变而出的隶书,个性强烈多了。后来收入拙著《民国书法史》。然对谢氏生平业绩知之不详。2002年6月,出席“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研讨会”,在会上邂逅常州博物馆叶鹏飞先生,谈起此事。不久,叶君寄来专集。故今又转为详细的介绍谢觐虞、谢稚柳两位前贤,于广大读者一定会有参考、借鉴意义的。
主要参考文献
谢伯子画廊编《谢玉岑百年纪念集》
夏承焘《天风阁日记》
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
廖静文《徐悲鸿一生》等
(作者为南京随园书社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