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桑愉是当代杰出的篆刻家,因过世较早,对其篆刻艺术的研究不多。本文从钩沉桑愉的生平、交游出发,历史地阐发其创作思想,揭示其以汉金文为基点、以“方刀治印”为特色与黟山派拉开距离自树一帜的艰苦历程,探讨其艺术作品内涵及其当代意义。文中讲述的桑愉生前交游中故事,亦是当代篆刻史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
关键词:黟山 汉金文 方刀治印 开派
一
我现住在扬州北郊建隆寺小区,每当我进城办事或会朋友,多半不是由玉带河大路迳直入城,而是绕道天宁门街。并不是我不喜欢玉带河两侧的新兴建筑群或闹市的风采,去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抒发一下灰色的情怀,实在是这条街蕴藉着太多的故事了,每从她身边走一次便可寻回许多失落的世界。
清初,一个从京师来的身披袈裟而内里却是明朱后裔的大和尚,他在扬州转了几圈以后,看准了天宁门街河沿的风水宝地,筑了一座大涤草堂,然后就在这儿定居下来,一住就是十年。在这十年中,他不仅作了许多价值连城的传世佳作,而且在这儿完成了直至今天仍然研究不了、探索不完的伟大美学著作———《画语录》。这个和尚名叫石涛。自从石涛定居天宁门街河沿以后,以天宁门街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就成了现代文人口头禅中经常提到的所谓“人才带”了。石涛之后,乾隆年间的声显一时的扬州八怪之汪士慎,高翔,金农,郑板桥,罗聘、方婉仪夫妇,或侨寓,或世居,都是紧紧挨着天宁门街,形成众星拱月之势。嘉道年间江南出了个才子,名叫包世臣,寄食扬州。他先住在扬州观巷的小倦游阁,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他又搬到天宁门街后的天心墩,大概也想沾沾这儿的风光灵气吧。后来他果然到江西去做了一阵子小官。嘉庆十四年(1809)九秋邓石如至扬州访包世臣于天心墩,包却去了东台,至深冬,包仍不归,邓受家书之催返乡。邓刚离开扬州,包第二天便回到天心墩。翌年邓病故于家乡,这成为清代书法篆刻史上一件憾事。
以上这些都是“过去的故事”了。至于现当代,说也怪,天宁门街又出了个足以令江苏人自豪的篆刻家———桑愉。
今天的年轻人,如果去天宁门街走一遭,也许怎么也不会想到,如今这般萧条冷落的小街,在清代和解放前是何等的热闹、繁华。解放前,天宁门街是老扬州出北门的主要通道,再加上街后穿城而过的水上通道小秦淮河与之比肩平行,这一旱一水的交通位置,就足以使这条老街长盛不衰了。解放前的天宁门街,不像如今这般,是个居民区,彼时街的两侧全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商店。每到春秋两季朝香之日更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在这条街的中段有一家远近闻名的桑恒顺香店,店主叫桑绶卿,为人儒雅好客,且能书善画,喜收藏,是其时为数不多的收藏家,和扬州文人墨客过往甚密。彼时每当扬州的书画文人进城,都要到桑宅后堂歇歇脚,吃杯茶,聊聊天。若凑得三五相逢,也便是桑恒顺文会之际。店主颇有马氏玲珑山馆遗风,慷慨解囊,为之热闹一番。其时如陈含光、鲍娄先、顾伯逵、何其愚、蔡四爷、孙龙父、王启明都是桑宅的座上客。
1929年2月7日,桑宅喜得贵子,其父高兴非常。希望这个儿子长大后,宛如一棵青松,成为国家栋梁之材,为这个儿子起了个宝松的名字,后来因这个孩子讨喜,又起了个名字叫桑愉。桑愉稍长之后,也许是受环境影响喜爱书画,尤爱操刀刻印,后为蔡四爷发现,喜欢了得,遂将其收为入室弟子。其时桑愉约为十六、七岁。
所谓蔡四爷,即蔡易庵(1899-1974)。名济,字巨川,号易庵,在家排行第四。世居扬州粉妆巷。毕业于北平艺专,满腹诗书擅长书画,尤以金石篆刻名震江淮。因富家出身,一辈子不知柴米油盐,总是无忧无虑地过着快活日子,对人亦极其随和,久而久之,人们便忘了他的名字,见面就叫一声“蔡四爷”。蔡四爷的岳丈陈氏为江淮名门。曾岳祖陈嘉树公为江西巡抚,岳祖亦舟公为安徽巡抚,岳父陈重庆官湖北盐运使。蔡四爷和其时誉满江淮的书画家陈含光为姻兄弟,一时并称“陈蔡”。桑愉有这样一位大篆刻家做老师,亦可谓三生有幸矣。古人云:入门须正,聘师欲高。这就意味着一个不走弯路的好前程。像桑愉进入艺坛之初,就碰到蔡易庵这样的好老师,在艺术界是不多见的。
蔡易庵先生在收授桑愉之初,并没有一开始就教其如何执刀、如何刻石,而是先教其临《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后又教其临《泰山刻石》、《史晨碑》、《张迁碑》等秦汉碑版(后来桑愉写得一手好篆书、好隶书便是得力于蔡先生的教诲)。蔡先生等桑愉书法初具规模后,方授以治印之道。起初,蔡易庵先生只许桑愉刻汉印,而且教其死守在“汉官印”之中。蔡易庵先生把一生的绝学全部交给了桑愉,对其成长寄以极大的希望。及至桑愉弱冠之年,就以一手醇正的秦汉印驰名大江南北,一时求其刻印者,旋踵不绝。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如《愈庐》、《传不习乎》、《若木先生》等印,就是这时期的桑愉的印章风格。
这些印章结体宽博而浑朴,行刀含蓄而稳练,布局均亭而端庄,真可达到“置之汉印而莫辨”的程度。这段时间里桑愉年富力强,每年在教学之余治印达三百方以上。孙龙父先生跋其印谱云:“白石老人以治印繁富自豪,自号曰三百石印富翁。若和君比之,真可谓自愧不如矣。”桑愉这期间在秦汉印方面所下的工夫,为他以后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任何一个有为的艺术家都不会满足于在前人的道路上爬行,都必须走自己的路。35岁以后的桑愉,在治印道路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于《乐观楼印章札记》中写道:
“摹体以定习,同性以练才”(《文心雕龙》),风格的独创也得学习前人,但只是出发点,而不是终点,否则“屋下架屋,愈见愈小”。
要冲出“秦汉”自辟蹊经,这在老前辈的眼里是“叛经离道”。当时议论不小,但他毫不动摇,他在《乐观楼印章札记》中又写道:
“风格在于独创”,“必然要寻出自己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高尔基),“文章切忌随人后”(黄山谷),治印亦然。
要冲出前人规模,就必须总结前人得失。因此,桑愉在这段时间里对近代印章各流派,诸如浙派、邓派、赵之谦、吴昌硕等派作了大量的摹习和研究。他于《札记》中对近三百年的印章史,作了这样论述:
丁龙泓出而文何旧,完白出而龙泓旧,赵之谦别开生面,吴昌硕出而前人皆旧。吴昌硕得力吴让之,笔画尚简尚直。盖印文蜷曲之笔,越后越少,至吴昌硕尽去之,质朴极矣。
印章之进步发展,都是由于旧的已尽失古法,忘典忘祖,而新作反从传统———秦汉印里继承,古法创以新意,立为一家。丁敬、赵之谦、吴昌硕无不如此,但是总得富有新意———时代气息。
桑愉要在继承秦汉的传统上开创有时代气息的印章新路。走丁敬的浙派?他常说“篆刻家晚年往往回到浙派或汉印中去,这是才尽力竭的表现”,这他当然不肯。走吴昌硕的路吧,他也不肯。因为,他认为吴昌硕派已统治印坛近百年,而且已“极矣”,走到了顶点,不可能有所发展。他最后选择了走黟山派———黄牧父的路子。他要在黄牧父的基础上再探金文、甲骨,闯“贵在自我”的新路。
印章之发展,自乾隆以后可谓流派纷呈,百花齐放,而桑愉为什么独独爱上了黟山派的印章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代印章史上的几个重大流派的兴衰和蜕变。以丁敬为首的浙派印章是近代印章史首先崛起的一个强大流派,他的成绩是在赵宧光、朱简、扬州八怪印章的基础上对秦汉印大量总结的结果。他发扬了秦汉的特色,以白翻朱,开创了朴质高古的浙派印章艺术。其缺点是对朱简的治印用刀,不能扬弃,刀锋过分外露,缺乏书卷气。继之而主宰印坛的是邓石如———吴让之号之曰“邓派”的印章,邓派的印章几乎是完全反浙派而行的。它的艺术特色是圆纵流美,把刻印和书法糅合起来,尤其到了吴让之可谓真正达到“书从印入,印从书出”、行刀如行笔的境地。这和浙派来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邓派印章多取法于汉碑额。这是和清中叶阮元、包世臣等人倡导北碑,清中叶金石家大肆搜寻研究碑版紧紧相连的。赵之谦生活的时代是吴让之的印章风行大江南北的时代,赵之谦早年对吴让之可谓推崇备至,也曾学过一段时间。但是赵之谦不甘为后,他在学习吴让之悟到难以超越之时,便另辟蹊径,把视角转向晚清朴学成果,取法商周彝器、汉镜、灯、砖、瓦当、六国钱币,开辟了自己的印章道路。赵之谦的白文印章大大发展了前人的治印方法,他能从汉镜、汉灯等文字疏散飘逸中去领悟邓石如“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通风”的艺术真谛,白文治印能大胆留空,有力地冲击了“缜密”、“匀称”的白文治印成法,使白文印见空灵,这是赵之谦的一大发明。其功绩之一,为后来齐派印章的诞生打开门户。吴昌硕是继赵之谦而起的被誉之为集前人之大成的“印林巨擘”,他在治印道路上能像赵之谦避开吴让之那样避开离他相近的赵之谦,取法吴让之,又因泥封是朴学中最晚出现的新领域,所以吴昌硕在涉猎商周金文、汉灯瓦当同时再偏师泥封,开创自己苍穆、浑厚的印章流派。近代印章中这种“相近相远”借重朴学开创艺术派流的“奥秘”,桑愉是早已看到了。他不止一次地说:“篆刻学之兴与朴学有关,亦与秦汉印及泥封出土有关。”桑愉在深刻研究近代、现代印章流派的蜕变之后毅然地舍吴昌硕而走黄牧父———秦汉金文的治印道路是极有道理的。
桑愉既舍吴昌硕,又为什么偏偏选定走黄牧父的道路呢?下面我们再谈谈黄牧父其人及其印章的发生、发展、艺术特色。

若木先生 桑愉 刻

观鱼胜过富春江 桑愉 刻

传不习乎 桑愉 刻

汉弇唐 桑愉 刻
桑愉 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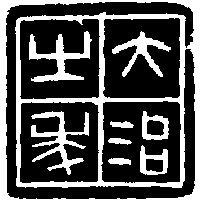
大治之年 桑愉 刻
黄牧父(1849-1908)名士陵,字牧父,安徽黟山人。少家贫,父死后肄业于清国子监。后从吴大澂游,学问大进。吴巡两广,黄入其幕府。相传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多半出于黄手。故黄对金文有极深的研究。吴大澂出任湖南,黄侨居粤中,专以书画篆刻自给。乔大壮于《黟山人黄牧父先生印存序》中评道:“黄作篆极渊懿朴茂之胜,治印自秦汉玺印外益取材钟鼎、帛币、秦权、汉镜、碑碣、陶瓦,故于皖浙两宗依次衰竭之后自树一帜,学者尊为黟山派。”黄牧父和吴昌硕(1844-1927)是同时代的印人,黄牧父比吴昌硕晚生五年,早去世19年,吴昌硕40岁左右在篆刻方面成就已很高,大有推倒一世空群雄之势。此时黄牧父才初露头角,50岁以后的吴昌硕印章几乎风行全国,被印坛推为“盟主”,而黄牧父此时开始从吴让之中脱颖,窥探新路。在一个强大的富于生命的印章流派刚刚兴起、全国绝大部分印人竞相摩习之际,要想另起锅灶,自创新路是要有一点拗拔的劲头。黄牧父毕竟是黄牧父,他毅然决然地走了自己的路。黄牧父和吴昌硕早年都曾在吴让之上面下过功夫,后来他们都把触角伸向秦汉,这一点经历大体相似。黄牧父完全不像与他同时代或稍后的李苦李、赵古泥乃至邓散木那样在吴昌硕的羽翼下发展,发挥自己的特长,成为吴昌硕派中的一员战将或发展吴昌硕派中的某一艺术特色,另辟一个支派。这样既可省力气,又能迎得众好。但是,黄牧父没有这样,恰恰相反,走上了无论是在行刀、走笔,乃至章法布局上和吴昌硕都截然相反的道路。例如吴昌硕学让翁重其笔势———“印从书出”,而黄牧父在学让翁时则重其行刀———“若无所视、神游太虚”;在其“变法”过程中吴昌硕重篆籀之意,黄牧父则重分隶之意,故吴昌硕行笔重圆浑,而黄牧父则重峻峭。吴昌硕在章法布置上偏师浙宗,主茂密、主均,故其印苍莽烂漫;而黄牧父在章法布置上偏师赵撝叔,主凋疏,主不均,故其印以淡泊、生拙见长。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吴昌硕处于鼎盛之时,黄牧父能如青峰傲傲兀立,在岭南与之遥遥相望,分区而治,开辟了岭南派印章艺术。近人有文评道:“黄牧父其篆刻成就更为突出,他治印初学吴让之,而后取法汉印,间用金文入印,章法疏密处理匠心独运,能在极险中得平衡,在平实中追超逸,刀法刚健,前无古人。”(《书法》1979年第四期《黄士陵印选登》按语)在吴昌硕逝世7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拿黄牧父和吴昌硕相比较,这样的评语似乎并不过分。

未名斋图书 桑愉 刻

欣然三次到黄山 桑愉 刻

无咎 桑愉 刻

无咎 桑愉 刻

饮瘿瓢馆 桑愉 刻
我们今天在研究桑愉印章艺术之际,必须洞察桑愉生活时代的印坛风向及黄牧父和吴昌硕分道扬镳、分庭抗礼的内在机理和心理过程。这个内在机理和心理过程也就是桑愉要创就“富有新意———时代气息”另立新派的内在机理和心理过程。也就是说,桑愉在选择黄牧父的同时,也承传了黄牧父的开派意识。换句话说,桑愉要扬弃的不仅仅是沉缅于秦汉印中的旧的自我,还要在继承黟山派艺术的同时对黟山派进行再扬弃,以铸就一个新的自我。这就是所谓“桑愉精神”的所在。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在还把桑愉看成黟山派中的一员,或说成是黟山派中的一位佼佼者都是不符合桑氏生前意愿及其创作心理过程的,当然也就看不懂,更弄不明白桑氏晚年的印章面貌及其深厚的印学内涵、美学机制。这从桑愉生前对黟山派的研究中大体上可以看出这种艺术倾向和创作过程。桑愉在《乐观楼印章札记》中写道:
黄牧父所作印,字法多变,分行布白亦好。巧则巧矣,浑厚不足。
又云:
刻白文要刚劲而有含蓄,用刀爽利而遒劲。黄牧父失之大爽无含蓄。黄牧父、吴让之治印用小刀,小刀治印锋芒毕露,气力不足。
以上这段文字大致写于60年代。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桑愉在继承黟山派的同时,已发现黄牧父治印过于精巧雕凿、用刀单一、浑厚不足等缺点,同时作了吴让之及其门人赵仲穆和黄牧父的对比研究,领悟到工具性这一美学性质对于印章创作以及印章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印学研究应当和创作实践相结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理论止步的地方是实践”。自此,桑愉在发展黟山派的同时,在印章创作的工具性方面进行了许多重大的工具性改革。印章面目一新,确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978年秋,沪上韩天衡兄因拍《书法艺术》电影专题片取道扬州。天衡和我说:“可否去看看桑愉先生?”我说:“应当去一次。”之后,在我陪同下韩兄来到桑氏老宅,这是当代两篆刻大家平生仅有的一晤。起初,桑的言语并不多,只是拿古印和古印谱给韩看。后来韩要看桑的近作。韩看后良久未置一词。忽然抬头问我:“桑先生的艺术特色是什么?”我未加思索地答道:“方刀治印。”韩反问道;“何谓方刀治印?”这下子把我弄懵了,一时无言以对,出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事后桑愉和我说:“那天怎么连方刀治印也答不出?”我说:“只是听孙龙父先生说过,实不知其详。”桑先生笑了笑说:“方刀者,非刀之方圆,而是指刀之笔意也。前人说,篆藏锋,隶铺毫。篆笔见圆,隶笔见方。故方刀者,是行刀传其隶意也。”
三
“方刀治印”是桑愉印章艺术的总特征。
桑愉是怎样在继承黄牧父印派的同时创就他的“方刀治印”这一艺术特色呢?其发展过程大致涉及到三个方面。
其一,黄牧父在开派过程中避开吴让之圆纵小篆之势,取法商周金文,而桑愉在“变法”过程中舍商周金文,重在汉金文上谋出路。这又为什么呢?就金文的内容来说,多为诰、诏、法、令,多为给下级官员、黔首百姓看的,要使大家看得懂,不仅内容上要从简,而且在文字字体上也要简明易认,这样才便于广泛流传。商周金文一方面是比较难认,笔势多见圆纵,而秦汉尤其是两汉金文是中国文字大变动时期,是简、隶、楷、草正在孕育产生之际,它们只在笔势上稍带大篆之意,而结体上见方,雄厚中见灵动和飘逸,有些字实际就很接近现代的简化字。要使入印文字行笔走刀厚重、朴质,当然以取秦汉金文为佳。这样易于克服入印文字的纤弱、气力不足的毛病。
其二,桑愉在使用的刀具及执刀之法上作了重大的改进,使之更适宜表现作汉金文的气质。前人治印多用小刀,3×3mm就算不小了,而桑愉刻印所用之刀为14×14mm,刀口角度为36度。桑愉说:“吴昌硕用刀主圆,赵古泥用刀主方。或称吴昌硕刻印以钝刀,殆刀刃成三角为钝角,外钝锋也,至有夸钝刀刻印甚至以洋钉代刀,谬矣。”桑愉常说:“欲善其事,先利其器。”故桑愉之刀是很锋利的。他认为印文之厚薄、巧拙,在于行刀之腕力和法度,而不在于刀的利钝,故桑愉主张用大刀、快刀。前人执刀之法多似写字之执笔法。即:“用大指与食指撮定刀干,中指辅于上,无名指、小指抵刀后中正刀锋。”(袁三俊《篆刻十三略》)以这种执刀之法行刀,力由肘传腕再达指,优点是灵活,缺点是气力不足。桑愉的执刀法是紧聚五指,握刀于掌中。用这种执刀法入石,力由臂达肘,再由肘至掌,这样力矩极大,刀或向前推,或向内旋转,挥动大臂,坚定沉着,洋洋洒洒,所向无前。此执刀法,酷似南朝王僧虔、唐张从申之握管作书法。用此法刻印,拙趣、浑厚、爽朗、生辣、险峻往往兼而有之。相传赵之谦、吴昌硕刻印亦用握刀法。观赵之谦印笔势较弱,而吴昌硕印结体茂密,多不可信。用握刀法刻印,宜乎印文结体疏散,字体行笔姿纵洒脱。而秦汉金文尚直尚简,笔势内松外紧,故能使印文洒得开来,得到良好效果。若桑愉刻的《饮瘿瓢馆》、《龙马精神》、《孺子牛》都是很好的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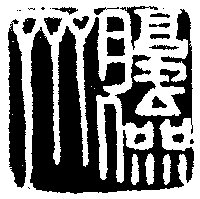
腹俭斋 桑愉 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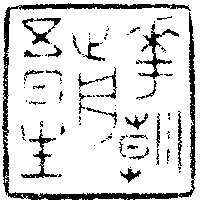
花朝前五日生 桑愉 刻

不期修古 桑愉 刻

石憙斋收藏之记 桑愉 刻

战斗正未有穷期 桑愉 刻
其三,桑愉晚年颇喜刻甲骨文,这又为什么呢?甲骨文系殷墟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因为这些文字是用石刀或铜刀刻在坚硬龟甲上或骨头上,故称为“甲骨文”,又称为“契书”。甲骨文的刻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格。武丁时代的雄浑豪放,帝乙时代的秀丽整齐,中期文字虽然有草率颓靡之嫌,亦有特殊风味。郭沫若于《殷契粹编考释序》中写道:“读者请试展阅第一六六八片焉。该片原物画为牛胛骨,破碎及存二段,而文字本能衔接。所刻乃自甲子至癸酉三十个干支,刻而刻者数行,中仅一行精美整齐,余则歪剌几不能成字。然于歪剌者中,都间有二、三字与精美整齐者之一行相同,盖精美整齐者,乃善刻善书者之范本,而歪剌不能成字者乃学书刻之摩仿也。刻鹄不成,为之师范者从旁捉刀助之,故间有二、三字合乎规矩。师弟二人蔼然相对之态,恍如目前,此实饶有趣之发现。且有此为证,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他又说:“甲骨文是信手刻上去的。要达到这样的技巧,是需要长期的艰苦练习的。”还说:“金文和甲骨文,实际是一个体系。甲骨文是用刀刻在骨质上的,故来得瘦硬,金文是用笔写软坯上而刻铸的,故来得肥厚而有锋芒。甲骨文乃至陶器上偶有用笔写的字,那感触便和金文差不多。”从上述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桑愉刻甲骨文印章,并不是为了以印章形式来炫耀自己认识几个甲骨文,而是通过刻甲骨文来体味殷人契书之用刀,以充足他的“方刀治印”。《古为今用》是学习殷契书所刻的一方甲骨文印章。此印在章法纵不成列,横不成行,错落分布,四字若孤立起来看,各字攲侧,几不成书。然而,此四字中“今”字向左边闪,“为”字“象”部向右闪,“手”部向上提;“用”字中间二划向下沉,“古”上部向上吊把下面“口”字放得特大。这样,全印众多方、圆、横、斜的笔画在一片动乱中闪出数块红地,而这些众多方圆并茂、横斜疏密的刚劲用笔也藉以安详地镶嵌在方寸之地,显得“违而不犯”。刻白文,白文用笔借红地取得平衡和谐,在古今印章中实不可多见。此印在行刀上深得契书之三昧,笔笔见起落,刀刀见变化,平直处见刚劲,宛转处见含蓄,涣散处见起伏顿挫,很见立体之感。这方印在章法上深得中期甲骨之飘逸洒脱之趣,而行刀上得武丁时期的雄浑豪放。从这方印我们不难看出桑愉在探索殷墟契书时所下功夫和取得的成绩。同时亦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在工具性改革后在艺术风格上的变化和成就。
桑愉师承黄牧父时,能进行大胆的取舍,纵观他所遗留下来的逾千方印作,这些印作向我们展示他近半个世纪的缩影,他所走过的是一条艰苦、诚实、百折不挠的探索道路。他不是谨守一家之法、殚思竭虑仅得其表的效仿复制家,而是一位以我国古老的文字艺术和篆刻传统为摇篮,勇于创新、勇于进击的探求者。桑愉生前在扬州举行过一次“怎样刻印章”的讲座,在讲到治印的刀法时他说:“黄小松说:‘治印章法七分,刀法三分,以章法为主。’依我愚见,对于已具有一定基础的印人来说,刀法要占七分,章法占三分。”乍听到很吃惊,现在细细体会是有一定道理的。朱简于《印经》中说:“刀法者也,传其笔法者也。”书法是运笔于纸上,刻印则以刀代笔施于石上,未有不谙熟笔法而能写好字的,当然也不可能有不知刀法而能刻好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足为怪了。

高吟肺腑走风雷 桑愉 刻

愉玺桑愉 刻

智铠制赠 桑愉 刻

百花齐放 桑愉 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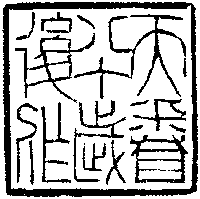
天眷八十岁后作 桑愉 刻
在这里桑愉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篆刻学论点,即以刀法融汇笔法、篆法,将笔法、篆法融于行刀之中的刀、笔、篆三法同一论的创作思想,颇见创意。这样,篆刻创作论中就合并为刀法和章法二大块,并趋同于书法创作论,可惜至今未引起有关论家的注视。这是我们在研究桑愉印章艺术时必须提到的。笔者认为这是桑愉对当代印学理论的建树之一。
桑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龙马精神》、《还未入门》、《扬州耿氏藏书》、《石憙斋收藏之记》、《天齐庆雷堕地》、《临岐意怅然》等印。这些印为桑氏晚年“方刀治印”风格定型后最具有的代表性作品中的一部分。这些印章在章法上不求奇,笔法上不求险,不肆意夸大笔道轻重,不滥觞边栏、印文之破碎,刀锋藏处不暗,刀锋显处不霸,笔画严陈处不板滞、涣散处不失法度,把书法的迟疾、顿挫、起伏、抑扬贯乎于行刀之中,一印之中往往把吴昌硕之苍穆、黄牧父之古拙、吴让之飘逸、赵之谦之空灵不自觉地融为一炉。从近代和现代印章发展史看来,印章艺术的发展始终随着书法及其朴学的发展逐渐壮大。解放后,我国考古学成果累累,桑愉能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上下求索、刻苦实践,最终锁定在汉金文方面问路。汉金文体势游动于篆、隶、楷之间,笔画多变且从简接近于今体字,更能适应当代受众的审美要求。这一前一后的相互照映,说起来易做起来难,它初步实现了古典篆刻向现代篆刻的转换,为当代篆刻印风格昭示了时代特征。这是桑愉“方刀治印”当代意义的第一层面。另一层面的意义在于:桑愉的“方刀治印”从入印文字实现了由商周金文向后汉金文的转换,入印文字在体势上得到极大的充实和丰富,克服了黟山派过巧、过爽之失;在刀法上,桑愉的“方刀治印”用大刀,法隶意,使其入印文字之笔道更沉着、更肯定、更朴质、更苍老,从而实现了雄踞印坛近百年的黟山派由黄牧父到罗叔子的嬗变终结,在蜕变过程中跳出个新的风格,实现了黟山派的凤凰涅槃。
至于桑愉印章能否算是开派之作,目前在同道中尚有争议。这是一件好事,欢迎引起广泛的争论,无论桑愉治印的得与失,均有]借鉴意义,因为他毕生在印章艺术上所耗费心血无不旨在窥探现代印章的方向及其出路上面。当然,他走过的路不是唯一的路子。
桑愉治印是非常勤奋的,也是非常谦逊的,他将每年刻的印蜕汇为一集,然后请他的老师易庵先生品鉴。1974年所集的印集,定名为《七四年集印》。这年深冬,他带着他的印集去看望病中的老师易庵先生。其时易庵先生已不能提笔了,正好著名书法家魏之祯先生在场,就由易庵先生口述魏先生代笔,写下以下一段跋文:
宝松近刻印,多取方笔,能开派者也。宝松能以此趣贯乎道行,可畏。
我以前给桑愉写文章时只引到这里。其实下面还有一句:
若能回到秦汉中则更好矣。
两段文字合并起来,它意思就比较明确了。后来,魏之祯先生又将这段文字写在桑愉的墓志铭上并刻在桑愉墓碑之碑阴上(碑阳为林散之先生书)。也就是说,魏老也同意蔡老的观点,作为定论并刻在桑愉的墓碑上,便可谓“铁笔”也。现在蔡、魏二老均已过世,我亦老矣,这段公案应有个了结,还桑愉一个公道。
易庵先生跋文云:“宝松最近刻印多取方笔,能开派者也。”这是说桑愉这一段时期的印制,不仅有别于其他历代印派,而且与黟山派亦不同,另树一帜,为新派,鞭辟入里的指出其特色为“方笔”。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方刀治印”之说。笔者认为,若不是艺术修养深邃的老金石家蔡易庵先生是作不出如此学术定位的。不过下面的话是:“宝松能以此趣贯乎道行,可畏。若能回到秦汉中则更好矣。”语气虽婉转深沉,却是否定。也就是说,老先生直到临终也弄不明白,他最喜欢的学生为什么要这样刻,并刻出这个样子来?
在撰写碑文时,我曾劝魏老把这句话删去,魏老不同意,板着他那副大家所熟知的面孔说;“他的老师就是这样说的,我不能改!”当时我两颊流汗,涨得满面通红,象吃了秤砣似的,也只好唏嘘了。心想:我的老太爷,这是写墓志啊。我们现在把易庵先生的话翻译一下,说得明白点。依蔡老的一生实践和宗旨,印章以两汉为高峰,若取法新意最好走六朝。六朝在印学上,是汉印的延续,仍是汉印,万变不离其宗。刻印应起于两汉,最后仍要归于两汉。否则,不足为训,亦可谓“叛经离道”。这就是蔡老的意思,实际上也是代笔人魏之祯先生的看法。其实,这并不仅是蔡、魏二老的看法,恐怕至今印学界仍有一部分人还坚持这种观点。它实质上涉及到篆刻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创作主体性、风格类型及流派与个性等问题的讨论。“师法秦汉”、“追踪秦汉”、“以秦汉为皈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印章创作、印章鉴赏的金科玉律。但是,秦汉印是秦汉人的真思想、真感情的外化产物,蕴藏着丰厚的文化遗产。形式可以重复,基于一定政治经济上的思想却不能重复。从此出发,“师法秦汉”、“追踪秦汉”、“以秦汉为皈依”这一篆刻创作法则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其实,我们在前面文字中已引了桑愉在《乐观楼印章札记》中的话:“风格的独创也得学习前人,但只是出发点,而不是终点,否则‘屋下架屋,愈见愈小’。”可惜这本《乐观楼印章札记》蔡老生前都没有见到,若是见到了,也许会说服老先生,支持他的学生勇于开派并自树一帜。反过来说,如果桑愉当时“谨守师法,不能逾矩”,仅能达到置于秦汉印中而不辨的话,我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桑愉还有什么可论的呢?在这里我们倒反觉得桑愉胆识过人悟性高,而易庵先生也应为有这样一位因开派饮誉当代印坛的学生而含笑九泉。
四
1977年春夏之交,扬州地委开了个欢送会。欢送文革期间下放扬州的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陶白返宁复职。陶白在欢送会上说:“扬州是文化渊源深厚、人才辈出的地方。我下放在扬州的这些年中,有两个人最令我叹服不已。一个是卞孝萱,一个是桑愉。希望你们以地方文化事业为重,人才难得,善待之。”陶老的话一出,惊动了扬州地委。卞老其时在北京,很快调回扬州师院(即今日之扬州大学)。而桑愉的工作,却出现了令人怎么也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困难,迟迟不能落实。最后总有好人帮助,落实到市七中教语文兼书法。时间大约在1978年2月。1979年元月9日,旅美画家朱晨光回扬探亲,又是一次老朋友聚会的好机会。因一时高兴,桑愉在宴会上仅喝了半杯色酒,不想当夜凌晨,高血压突发身亡,年仅51岁。数月后,扬州一代书法大家、“江苏书坛四老”之一孙龙父先生因脑疾于5月1日归道山。这一年是近百年来扬州书坛最灰暗的日子,不到半年,扬州书坛竟失去了二位宗师,一下子变得群龙无首。失去最坚实、最有号召力的两根中流砥柱,使之元气大伤。时过二十多年,这口气还没有恢复过来。桑愉的早逝不仅震动了扬州,而且震惊了南京的书坛泰斗林散之先生。林老得知桑愉过世的消息后,失声而哭,泪如雨注,撰下一联以寄哀思:
君病不知,君死未闻,离别感匆匆,哀地频抛瓜步雨;
我生多难,我老无成,友朋嗟落落,伤心空溯广陵潮。
其惜才之深,悲友之戚,可想而知矣。
下面我们谈谈桑愉在当代印坛的艺术定位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对桑愉先生及其印比较陌生,以为是当下印坛推出的新人,以致产生困惑。这是对当代篆刻史及江苏印坛格局缺乏了解之故,198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丁吉甫先生主编的《现代印章选集》,也是开国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现代印章选集。这本集子从全国17个省市数百家印人中遴选了90家,作为现代篆刻艺术的代表。其中包括齐白石、邓散木、来楚生、罗叔子、傅抱石、方介堪、沙孟海、田原等当代名家,还有当时被认为是中青年实力派的韩天衡、黄惇、童衍方等,而桑愉即在其中,这是其一。其二,该选集有的占一页,有的占两页,还有二人合页的,而桑愉是为数不多独占两页作者中的一位。可见丁吉甫老先生对其印艺的首肯和激赏。这已是26年前的事了。丁吉甫先生编这本集子及其出版经过至今历历在目,态度是极其认真的,而且是极有分寸的。其时我和丁先生的关系很好。先生和我说“不是说你刻的不好,这一次你的资历不够”,所以没有选入。由此可见一斑。1982年我应陶白先生之请在《南艺学报》上撰写了一篇《桑愉印章艺术初探》的文章,全面介绍桑愉篆刻成就,为同道首肯,在书法印章界有一定的影响。1986年我于杭州西泠印社作客,由老友李伏雨之子李早陪同,游览了西泠印社仰贤亭。李早于藏印楼取出桑愉为该社刻的《临岐意怅然》、《唯有交游旧》二方印后,对我说:“这个柜子里所藏的印,是近年来印社请全国名家所刻的,这里面我最喜欢、最佩服的就是你们扬州的桑愉先生的印章了。桑先生近况如何,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玩玩。”我黯然地说:“桑先生前几年已仙逝了。”李早十分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可恨同时不相识’,真的要‘几回掩卷哭曹侯’矣。”这也是旧话了。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类书法篆刻大展兴起,塑造了一批书法篆刻新秀,这批新秀便成年轻人的追星族,那些曾被丁吉甫先生揽入《现代印章选集》的有成就的篆刻家其中大部分已不为年轻人所知,桑愉先生大概是在这样情况被陌生化了。但这只是存在于当今的年轻人中,而在稍有资历及年龄稍长的人中,桑愉这一辈有成就的老篆刻家的名字,仍然时时在耳边响起,令人怀念文革前的那一片自由生长、有根有叶、不为名利所驱的艺术天地。我也有这样的感受,目前要写一部当代篆刻史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我们对“五四”以来全国的各个山头尚未清理,对全国各个山头的领军人物还未作深入的个案研究,在这种情况作煌然大论是不适时宜的,无论是丢了哪个山头还是对哪个领军人物、或是评价失误都是愧对历史愧对故人。如何评判当代艺术家乃至篆刻家?第一条,凭作品说话,之后从作品亮相中折射出来的学养、功底、风格、个性、流派开创性等方面分析。至于桑愉的篆刻在当代篆刻史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本人以为应处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的一位。我相信这恐怕不是我一人的看法,当代人中自有眼睛。例如故友萧高洪兄,生前曾和我谈及过桑愉并将其写入他的《篆刻史话》。
桑愉的篆刻,颇得高二适、林散之两先生的赏识。现将二老的赠诗录下,以示我们对桑愉先生的怀念。
高二适先生赠诗云:
金陵印人吾皆识,晚得扬州桑阿松。
刀法超奇篆法古,羡君功深愈从容。
昔人佩印如斗大,赫弈功名胡为者。
我今羊薄老江东,累累之章比素封。
吁嗟呼,何时乞得书堂九万纸,
约君游戏墨池水,凿石攻书安止止。
该诗的题目为:《桑宝松为余作两面印二方,长歌奉谢一首》。
林散之先生赠诗云:
笑子不能务正业,业余又向纸堆钻。
可怜毛笔兼刀笔,倚取飞神石上刓。
搜取精灵夸上流,佩觹雅欲自封侯。
深刻浅挖寻常事,赢得声名两字留。
日日归来弄瓦当,千秋遗孽蔡中郎。
赏心自得窗前月,镌就名章号素王。
邗沟连日雨丝丝,我忆斯人吴让之。
春水断桥二十四,更于何处觅宗师。
该诗的后跋为:小诗四首赠广陵桑愉子,并示刻印诸同人兼呈孙龙父教授一粲,如何?七三年四月十五日散之于扬州荇庐。
按:林老诗中的“素王”见《汉书·董仲舒传》:“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文”者,法规也。汉代一些研究《春秋》的儒家认为孔子修《春秋》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也。也许林老在此有“素王”之叹,六年后,至桑愉过世时方有“伤心空溯广陵潮”之悲。
(作者为扬州教育学院教授)